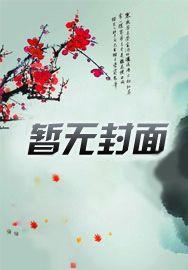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笑谈两晋南北朝:三百年乱炖一锅 > 第520章 刘宋后废帝刘昱 权力培养皿里的超级霉菌及其荒诞毁灭史(第1页)
第520章 刘宋后废帝刘昱 权力培养皿里的超级霉菌及其荒诞毁灭史(第1页)
序幕:龙椅上的小恶魔
公元472年的建康城(今南京),南朝刘宋的皇宫中正举行一场看似庄严的登基大典。九岁的刘昱身着略显宽大的龙袍,在文武百官复杂的目光中,摇摇晃晃地坐上那象征至高权力的龙椅。此刻,恐怕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看似懵懂的孩子,将在未来五年里,以他异想天开的暴力美学和层出不穷的荒唐行径,为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刘宋王朝,亲手挖掘坟墓,并奏响最后一曲亡国之音。
刘昱,这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顽童暴君”,用他短暂而炽烈的一生,活生生地证明了:权力落在错误的人手中,就像把核按钮交给一个熊孩子——其破坏力不仅惊人,而且往往充满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色彩。他的统治,如同一场席卷建康的飓风,所过之处,只留下一片狼藉与无数冤魂。
如果古代有吉尼斯世界纪录,刘宋后废帝刘昱绝对能荣膺“最具创意暴君奖”。这位皇帝把皇宫当游乐场,拿朝臣当玩具,用刑具当文具,最终在七夕佳节被自己的“玩具”反杀——堪称南朝第一作死小能手。他的故事,是一部混合了权力、人性与荒诞的黑色幽默剧,让我们在瞠目结舌之余,不禁思考:当绝对权力落入一个心智未熟的孩童手中,会催生出怎样一朵畸形的恶之花?
第一幕:混乱成长——从东宫到龙椅的扭曲之路
场景一:根植于血脉的混乱基因
要说刘昱,不得不先提他那颇具“特色”的家庭。他的父亲,宋明帝刘彧,在登基前曾有过一段不堪回的岁月。因其体型肥胖,竟被自己的侄子、前废帝刘子业戏封为“猪王”,受尽侮辱,甚至一度性命堪忧。在这种极度压抑、扭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刘彧,其心理状态难免受到影响。而刘昱,正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降生的。
史载刘昱“幼而狂狷,喜怒无常”,用今天儿童心理学的眼光来看,这活脱脱就是多动症加狂躁症,并伴有严重反社会人格倾向的典型案例。可惜,在那个时代,既没有心理医生介入,也没有特殊教育疏导,围绕在他身边的,只有唯唯诺诺的侍从和战战兢兢的老师。他旺盛的精力与破坏欲,在东宫这片小小的天地里已然初露锋芒。
场景二:当熊孩子掌握生杀大权
命运的转折来得突然。公元472年,宋明帝刘彧病逝,年仅九岁的刘昱被推上了帝位。一个刚刚还在为背不出书而烦恼、可能还会因为抢不到糖吃而撒泼打滚的小学生,突然被一群人跪拜着告知:“恭喜陛下,现在整个天下都是您的了,所有人的生杀予夺,尽在您一念之间!”这对刘昱而言,无异于打开了一个没有家长监管的、世界上最豪华的游乐场。
辅政大臣的劝谏?在他听来如同老和尚念经,枯燥又烦人。太后的训导?更是左耳进右耳出。他很快就现了比捉蟋蟀、放风筝更有趣、更刺激的游戏——真人版“大逃杀”。只不过,在这个游戏里,他是唯一的、规则随心的猎人,而满朝文武、宫中侍从乃至京城百姓,都成了他随时可以“淘汰”出局的玩家。权力的潘多拉魔盒,被一个孩子轻易地打开了。
第二幕:暴政实录——皇城里的恐怖游戏与行为艺术
场景一:皇帝的“移动刑具包”与日常“打卡”
现代小学生书包里装的是课本、文具和零食;而刘昱皇帝的“标配行头”里,装的却是针、锥、凿、锯等一应俱全的全套刑具。他堪称“移动执法”的鼻祖,将恐怖统治从朝堂延伸到了街头巷尾。
据《宋书·后废帝纪》和《南史》记载:“昱常以针椎凿锯之徒,不离左右。稍有不惬,即加屠剖,一日不杀,则惨然不乐。”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咱们的皇帝陛下,一天不杀人,就跟现代网瘾少年一天没连上i-Fi一样,浑身不对劲,看谁都像欠了他八百万。
于是,每日的上朝议事,对大臣们而言,不啻于一场生死未卜的俄罗斯轮盘赌。谁也不知道今天出门前吃的早餐会不会成为最后一餐,皇帝那“杀人灵感”的小火花,会否因为自己今天腰带系得不对、咳嗽声音太响,甚至是眼皮跳了一下而突然迸。大臣们出门前与家人含泪诀别的场景,在建康城的高官住宅区,几乎成了每日定时上演的悲情剧。
场景二:暴君的“创意行为艺术”集锦
刘昱的暴行,常常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残忍,带上了一种现实的、令人匪夷所思的荒诞色彩,堪称古代版的cu1t片现场直播。
妇产科的终极噩梦:他偶然闯入一户正在分娩的民宅,目睹产妇痛苦挣扎,非但没有丝毫同情,反而突“奇想”,亲手将已成形的胎儿从母体中强行拽出,并当场踩碎。更令人指的是,他做完这一切后,竟能哈哈大笑,扬言要“为天下所有的产妇接生”。这种反人类的“行为艺术”,其创意之惊悚,即使是最追求感官刺激的现代恐怖片导演,恐怕也要甘拜下风。
“肚脐”箭靶与萧道成的生死一刻:某年盛夏,他看到大将军萧道成裸身躺在院中纳凉,那圆滚滚的大肚子立刻激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兴致勃勃地走上前,以萧将军那醒目的肚脐为中心画了个圈,作为箭靶,拉满弓就要射。千钧一之际,左右侍从急中生智,劝道:“陛下神射,一箭毙命就不好玩了,不如用软箭(去掉箭头的箭)试试手感?”萧道成这才惊险万分地捡回一条命。这一幕“肚脐危机”,不仅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瞬间之一,也深深烙印在萧道成的心中,为日后刘宋的覆灭埋下了一颗关键的种子。
“张五儿”的驴与无差别攻击:刘昱对建康城的骚扰是全方位、无差别的。他几乎天天出行,“从者并执鋋矛,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逢无免者。”民间甚至流传着“刘昱出行,鸡飞狗跳”的顺口溜。有一次,他闯到右卫营(禁军驻地),竟然和妓女老板娘吵架,一怒之下,把营房给烧了。还有一次,他见到一名叫张五儿的百姓牵着一头驴,觉得驴叫声太难听,二话不说,亲自将驴杀死还不过瘾,顺带把倒霉的张五儿也一并解决了。在他的统治下,建康城“商旅废业,白日闭门”,繁华帝都,几成鬼蜮。
场景三:朝政?那是什么,可以吃吗?
对于皇帝的本职工作——处理朝政,刘昱表现出极大的不耐烦。史书说他“一月之中,殆废二十九日”,平均每月上朝一天,其余时间都在进行他的“街头行为艺术”和“宫廷恐怖游戏”。朝廷机制几乎完全停摆,政务堆积如山,奏章蒙尘。而他,或许正忙着给他的“移动刑具包”添置新装备,或者策划下一次出行的“惊喜”环节。国家机器在他手中,变成了一辆无人驾驶、横冲直撞的马车,直奔悬崖而去。
第三幕:权力失衡——朝堂暗流与叛乱烽火
场景一:叛乱——刘昱时代的“土特产”
一个如此荒唐的皇帝坐在龙椅上,天下若不生变,那才是怪事。刘昱在位虽短,但刘宋皇室内部的大型叛乱就生了两起。
474年,桂阳王刘休范之乱:这位皇帝的叔祖,眼看朝政被小皇帝搞得乌烟瘴气,觉得“清君侧”(或者说干脆自己上)的机会来了,遂起兵直指建康。朝廷一片恐慌,关键时刻,正是那位肚脐差点中箭的萧道成挺身而出,沉着指挥,平定了叛乱。此战让萧道成一战封神,在军中的威望与实力急攀升。
476年,建平王刘景素之乱:又一波宗室力量不满现状,起兵造反,结果同样被镇压下去。这两场叛乱,虽然都被扑灭,但其影响深远。它们如同一次又一次地为刘宋王朝“放血”,让这个本就因内斗而虚弱的帝国,变得更加摇摇欲坠,同时也极大地消耗了本就所剩无几的宗室力量。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刘昱的胡作非为和引的动荡,客观上成了萧道成崛起的“最佳助攻”。每当有叛乱生,小皇帝和他那混乱的朝廷就不得不依赖这位能力出众的大将军;而萧道成每平定一次叛乱,其权力、声望和势力就壮大一分。这就像一个自作自受的死循环:刘昱制造混乱->混乱引叛乱->叛乱需要萧道成->萧道成权力更大->刘宋皇权更弱。
场景二:众叛亲离——从太后到侍从的离心离德
刘昱的暴政,最终让他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因恐惧而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太后也想“退货”的儿子:当王太后(刘昱名义上的母亲,实际上是其父刘彧的皇后)看不过眼,多次严词劝诫他时,刘昱的反应不是反省,而是恼羞成怒。他竟命令御医配制毒药,打算送这位“多管闲事”的母后上西天。太后闻讯,悲愤交加,对左右说:“拿刀来,剖开我的肚子看看,我怎么就生出了这种儿子!”——能让名义上的母亲都想“剖腹退货”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实属凤毛麟角。
侍从的恐惧与逆袭:那些最贴近皇帝的近侍、卫兵,表面上唯唯诺诺,实则终日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之中。因为他们最清楚——在刘昱眼中,他们不过是会呼吸的、稍微高级一点的玩具,随时可能因为皇帝一个不高兴、一个怪念头就身异处。这种朝夕相处、如履薄冰的恐怖,最终凝聚成了反叛的巨大能量。杀机,已在宫廷最深处悄然酝酿。
第四幕:七夕惊变——一场荒诞的戏剧性终结
场景一:最后的“浪漫”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