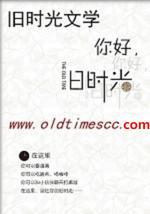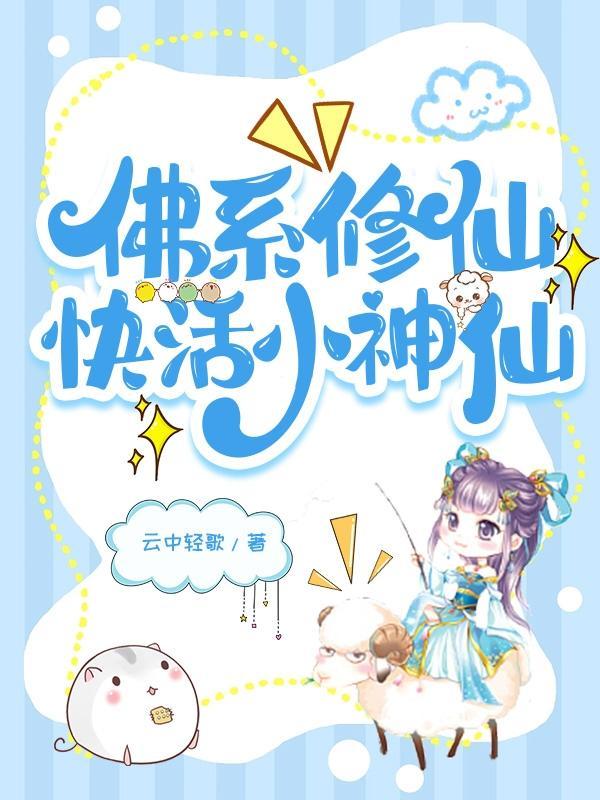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大明:我在洪武当咸鱼 > 第229章 真是大赚特赚(第3页)
第229章 真是大赚特赚(第3页)
“宋利,冯胜他们有无新奏报?”朱元璋的声音透露出难以掩饰的急躁。
“这都是三天前的奏报了!”
此时,距冯胜与蓝玉大军出征已逾一月。
大军在外,朱元璋怎能不牵挂?胜败倒在其次,那些残元与土司的散兵游勇,对大明将士而言,并非不可战胜。但远征之事,远非胜负所能概括。攀山越岭、遇水搭桥,稍有不慎,便会导致人员折损。加之大军出征,后勤必须跟上。一万大军行动,背后至少需要五万辅兵、民夫支援,还需朝廷各方协调。
这些问题,内阁虽会先行审核,但最终仍需朱元璋定夺。而他本就极为重视军事,自然耗费不少心力。
“回陛下,您手中的已是最新奏报。”小内侍答道,“或许晚些时候会有新的消息传来,冯大将军行事稳重,不会贸然行事。”
宋利的答复迅,却未能平息朱元璋内心的焦躁。
“他或许安分,但你岂会忘却,蓝玉仍在他身旁!”
“那老家伙在侧,天知道会惹出什么乱子!”
“蓝玉一旦冲动起来,十天半个月音讯全无,也不足为奇!”
显然,朱元璋对这些老部下的性情了如指掌。
蓝玉作战勇猛无比,偏偏好行险招。
他出战,非胜即败,从无僵持。
胜利时自然皆大欢喜,可一旦战败,亦是令人头疼不已。
然而,大明又确确实实离不开这位猛将。
毕竟,他的勇猛无可否认。
正当朱元璋为远征军忧心之际,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宁静。
“陛下,颖国公傅友德有急报呈上。”
“嗯?惟学的奏报?他不是该在海上吗?”
朱元璋满心疑惑地从宋利手中接过那份显然历经波折的奏报。
确认封口红漆完好无损后,他拿起一柄金光闪烁的小刀,轻轻划破了蜡封。
这是一封藏于竹筒、蜡封红漆的密函。
此等函件,胆敢阻拦或私拆者,一律处以死罪。
因能以此法传递的,必定是重大之事。
朱元璋不禁皱起了眉头。
若非这封奏报,他几乎要忘却了颖国公傅友德及其麾下的三千大军。
他们出海后,便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毕竟,大海之上,信息传递实为艰难。
上次收到傅友德的消息,是在一个多月前他刚到目的地时来的平安信。
转眼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不知傅友德那边情况如何。
朱元璋小心翼翼地从竹筒中抽出一份紧卷的绢帛。
匆匆一瞥,只觉头晕目眩。
显然,为了详尽汇报且受限于绢帛大小,傅友德的亲笔奏报写得极为紧凑。
朱元璋望着那密密麻麻的字迹,眼花缭乱,索性将绢帛递给宋利。
“宋利,你给朕读一读!”
“朕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宋利接过绢帛,大声朗读起来。
“吾皇万岁,臣傅友德与三千将士,于万里海疆之外叩拜。
一月前,臣已抵达与大明接壤的安南。
原本以为,需以武力让这些番邦见识大明的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