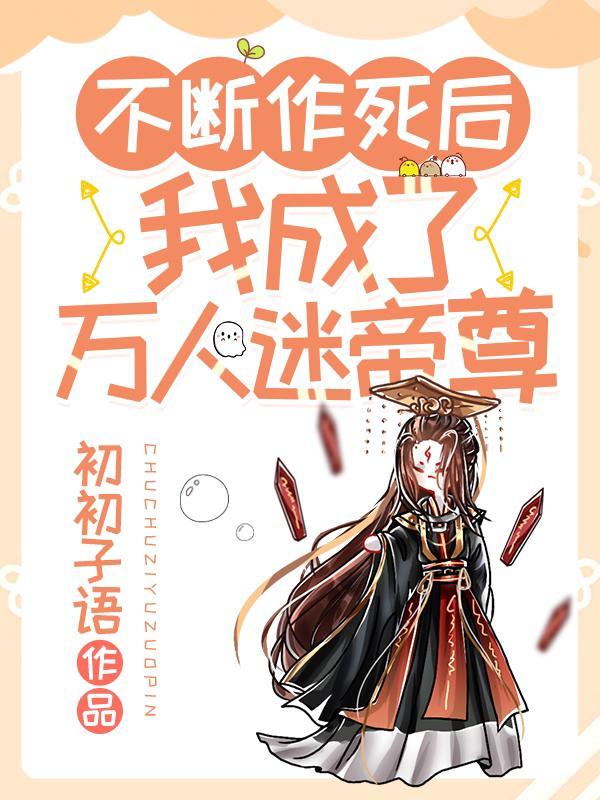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穿成哥儿下一秒 > 第103章 该受万民香火供奉庙堂之上(第2页)
第103章 该受万民香火供奉庙堂之上(第2页)
宋亭舟神色未变,“科举取士,乃是圣上亲掌,以文章定优劣,以德性衡去留。”
他平静地看向那说话的考生,“会试第二,扬州府程万里,你的文章我看过,均田当审利弊疏,虽意在济贫抑兼并,然丈量繁难,授田扰民、赋役紊乱,徒动国本,不若澄吏治、轻赋役以安民?”
程万里面色自傲,“正是学生所作,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如冉大人评判那样,其实程万里的文章做得不错,引经据典,字字珠玑。
但他问出这句话之后,亲眼见到宋亭舟眼底流露出几分讥诮,羞愤难当,口不择言道:“学生拙作既入不了大人的眼,不知大人又有何见解!”
对朝廷命官如此出言不逊,便有刑部的官员想上前喝斥,却被宋亭舟拦住,他官袍上绣着的锦鸡羽毛艳丽,象征着文采和威仪,然而文雅从不代表实干,做官也不是光靠一手好文章。
“丈量之难,较之百姓难以果腹之困,孰难?授田之扰,比之佃户纳租之辛,孰苦?你笔下辞理明切,看似有理有据,又是否亲至田畴,体佣耕之苦?”
不和你们掰开揉碎说明,你们便不知其中道理吗?
“学生……学生……”程万里一腔热流直冲面颊,面皮涨得通红,被质问得说不出来话了。
宋亭舟本可以不搭理这些考生,直接走开,眼下不会有人敢拦,可他挺着如松似柏的后脊,眼神黑沉沉地扫过面前被罢黜的考生们,哪怕没有故意施压,也带着让人心神一凛的压迫感,让这些考生不自觉警醒起来,凝神倾听。
“本官便是乡野出身,从未听过哪个村子有荒田而不耕,若有懒汉宁可饿死不种,自然有其他人想种。再来佃户也是普通百姓,并不低贱,不该被乡绅地主层层剥削,终其一生连温饱也难。田产是百姓的命,天下何人能离开粮食?你们该了解的是怎么解决那些麻烦,而不是投机取巧,认为一成不变才是好,会读书的进士太多了,皇上现在要用的是肯脚踏实地做实事的人,本官这样说,你们可懂自己是为何落榜的了?”
程万里等想辩驳他们没错,可却不知该如何去辩,内心深处有道声音在拉扯他们,宋大人说的才是对的。
冉大人等宋亭舟说完不免也感叹一声,“为臣者,本该协理阴阳,上承天子,下抚黎民,如此才称得上的一句官。你们该扪心自问,是图个金榜题名、光耀门楣,还是要躬身入局、为一方百姓谋福祉?”
人群里霎时静了静,来的都是一群热血青年,接连被两位大人质问和点拨,心中的迷茫与不甘如被晨雾驱散,渐渐清明起来。
是啊,他们寒窗苦读十数载,所求究竟为何?难道仅仅是那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风光?还是为了能在朝堂之上,为黎民百姓出一声呼喊,做一些实事?
方才的羞愤与难堪,此刻竟慢慢沉淀下来,化作一种沉甸甸的反思,想起了自己在时务策中写下的那些看似宏远却略显空泛的论调,垂眸盯着锦靴上的金丝云纹,矜傲的眉眼染上几分局促。
宋亭舟见他们神色变幻,知他们心中已然有所触动,便不再多言,转身对冉大人等人略一颔:“诸位大人,时辰不早了,我等也该回府了。”
众人相继告退,宋亭舟临走前背对着江彦等人,脚步微顿,却未回头,只留下一句低沉而清晰的话语:“若真心向学,何惧从头再来;若心系苍生,何处不可安身立命,三年后,再来回我今日之问吧。”
琼林宴也叫恩荣宴,第一批走的自然是考官们,接下来便是新科进士,同样人数不少,礼部门前的人员众多,一时半会都散不开。
孟晚坐在马车里玩扇子,听外面蚩羽说了句“大人”,便知道是宋亭舟回来了,旋即车帘被人从外面掀开,宋亭舟着一袭绯袍进来,尚未坐定,便先将头上的乌纱帽给摘了。
“搞定那些落榜的考生了?”孟晚放下折扇,把他的乌纱帽抱到自己怀里,扣着上面的玉珠玩。
宋亭舟挨着孟晚坐下,左臂横在他身后,将他半圈入怀里,“年轻气盛,尚未被世家凉薄伪善的风气所侵腐,可雕琢一二。冉大人已经起了爱才之心,苏州会元江彦,极可能被他收入门下。”
“哈哈。”孟晚似笑非笑地说:“冉大人怎么看见哪个都想收?是不是看江彦长得俊?”
宋亭舟闻言,本来松弛的眉头顿时皱成一团,“俊?”
不过是白了一点罢了,手无缚鸡之力,个头还不如晚儿高。
空气中似乎飘散出一点淡淡的酸,孟晚心里的雷达滴滴作响,立即熟练地岔开了话题,“听说卢溯中了二甲,他在琼林宴可单独找你说话了?”
宋亭舟冷着脸捏了他鼻尖一下,“只说了两句,明天他和其余几位岭南学子会一同上门拜访。”
卢溯一行三人,考中两人,还都混上了二甲。若不是被罢黜的南地学子太多,他二人顶多考个同进士。考前是要避嫌,如今都考完了理当上门拜访,除了他们之外,其余考上进士的和落了榜的都约好了要一起上门拜访宋亭舟。
“那等回家后我叫桂诚叮嘱看门小厮,明早若是他们来了也不必等着,直接叫进来。”
蚩羽驾着马车又走了两条街,在一条隐蔽的小巷外勒停了马匹,“夫郎,方庄头在这儿等着呢。”
刚才带着老乞丐走的老人凑到马车前,老乞丐则是在巷子里捧着他的碗。
方庄头气质一变,沧桑的脸上又是激动又是感慨,眼眶汪着泪,声音哽咽难忍,“夫郎,原来我们老爷真的还有人记得,他没白死,他死的……值吗?”
方孺山早就死了,死在那条入京的路上,苏州的士族怎么会让他有机会被三司审讯呢?苏州府布政司怎么会让他有辩驳的机会?不要小瞧这些土皇帝在当地一手遮天的本事,便是皇上派下巡抚御史来他们也敢整治,当时远赴昌平的王瓒就是个例子。
皇上赐给孟晚两座皇庄,其中一座被孟晚当成嫁妆添给阿寻了,方庄头他那座皇庄的庄头,是楚辞他们从岭南回京时救下的老人,他无以为报,只说给大官做过管家,阿寻便让他管理庄子。
孟晚不放心来历不明的人,亲自下场审讯一番,才审出些端倪。
至于这个乞丐,纯粹是桂谦随便找来的。
孟晚反问难忘旧主的老人,“怎么不值?二十年后,还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不信贼人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苏州府所有贫民百姓也永不忘怀他们耕种的田地是方大人硬生生从世家手里夺出来给他们的!”
连宋亭舟也神情晦暗不明,“方大人,早晚会沉冤得雪,他是济世安民的好官,不该悄无声息的泯灭,而是该受万民香火,供奉庙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