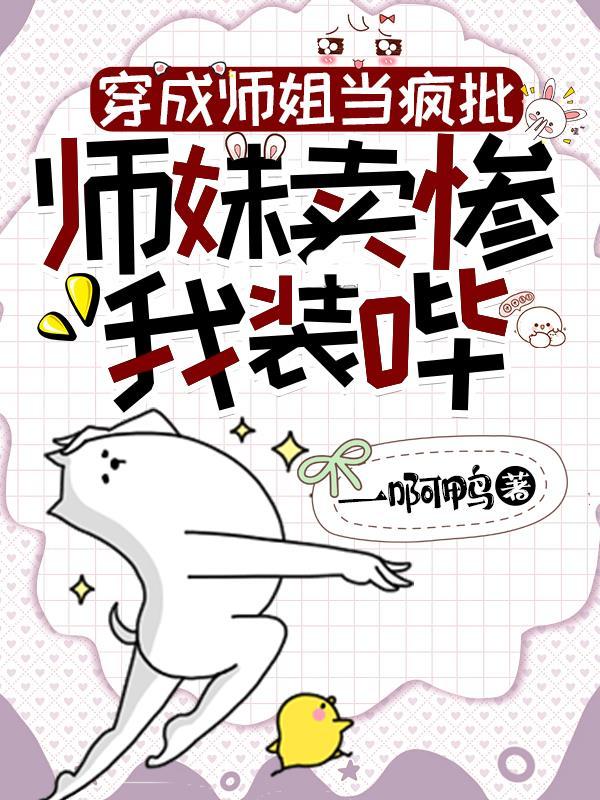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穿越之农家独苗苗的科举之路 > 第702章 刘盛远也回来了(第2页)
第702章 刘盛远也回来了(第2页)
“他还不到三十,这个年纪的举人,那肯定还要再考的”,张平安点点头,很理解。
“他从前读书就不错,有天赋、又勤奋,也算意料之中了”,金宝也跟着点点头。“不过他要给他祖父迁坟,看来是以后不准备再回来了!”
“是这样!”罗福贵很遗憾,“听他的意思,他们家祖籍就是洪州的,以后基本就是在南昌府定居下来了,他这次回来主要也是因为他父亲身体抱恙,不能回乡,他才赶着回乡祭祖,希望能完成他父亲的临终所托。”
“刘伯父身体不好吗?这还真是……唉!”金宝叹一口气。
“是啊,他母亲早已在南昌府病逝,就剩他父亲了,这是他父亲的心愿,他为人子的当然要回来了”,罗福贵点头。
他母亲也在战乱那几年去了,所以他很理解刘盛远。
几人一时静默,生老病死就是如此让人无力。
……
“福贵,那杨夫子还在书院吗?”看气氛静默,片刻后,刘三郎忍不住打听道。
“杨夫子?”罗福贵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是谁。
“就是以前青松书院的武夫子,教学子们骑射的”,刘三郎心里沉了沉,解释道。
“书院里早都没有武夫子了,更没有马,人都吃不饱了,学生也不多,如何能有条件再教骑射”,罗福贵摇了摇头,并不知道杨夫子的去向。
看几人一脸关心,罗福贵想了想,起身道:“我来青松书院时日也不太长,不如我去问问山长,兴许他知道呢?山长是从前书院的老人了!”
说完就要出门去。
“这样,我们一道去吧!”张平安起身道。
再怎样,没有让福贵去跑腿的道理。
“也好”,罗福贵没拒绝,“山长早就想去拜访你们了,就是你们今日不来,估计明日一早他也要去驿馆的”。
几人刚出门没走多远,青松书院如今的山长便迎上前来。
年约四十,态度热情但不失分寸,不卑不亢的,气质儒雅。
张平安知道如今的山长依然是林家人,只不过是林家旁支的旁支,跟林家本家已经隔得很远了。
要不当初南逃也不会落下他们。
这位山长据说以前在青松书院做过夫子,但有些透明,存在感不强。
张平安印象不深。
两边寒暄过后,刘三郎说明来意,林山长捋着胡须回忆道:“杨夫子我知道,咱们书院这一二十年来,也就他一位武夫子,战乱那几年他也没逃,一直在县里,好像还被逼着在乱军的军营中做过杂役,后来乱军走的时候他想法子逃出来了,扛过了饥荒,一直活到了新朝初立,但是到底年纪大了,那几年饥荒把人都拖垮了,后来病逝了,当时还是书院里几个老人帮着安葬的。”
“已经死了?”刘三郎不确定道,哪怕心里有些预感,他依然感到很难过。
张平安也想起那个洒脱又不羁的男子,一时间也沉默了。
杨夫子真的是这个时候少有的活的热烈坦诚而又自由的人。
片刻后,张平安才叹了一口气问道:“葬在哪里了?可否带我们去看看?”
说完又吩咐吃饱赶紧去买些祭品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