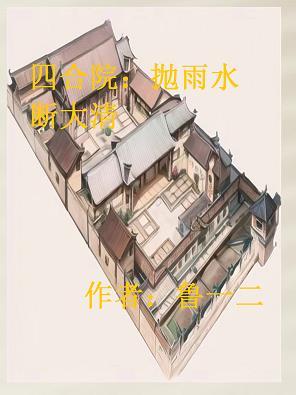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和离前夜,她重生回了出嫁前 > 第187章 宁芙之计婧成之心(第2页)
第187章 宁芙之计婧成之心(第2页)
李秋生站在一侧,等着孟泽找人确认这药方。
谢太医认真瞧了瞧方子,道:“这方子,确实是微臣开的,太医院的几位前辈,都曾瞧过这方子,不过浮生梦,只有慕神医那有,是以臣无法给世子妃开药。”
孟泽又找人验过这开方的纸张,确认无误后,才派人私下将这药方,送回到了慕若恒的茶庄。
“方子并无蹊跷?”李秋生问道。
“我已验过,并无大碍。”孟泽心不在焉道,“不过你这般细心,倒是个好习惯。”
眼下他不能得罪宗肆,宁芙是想为宗肆开枝散叶,若是他知晓这方子出现在自己手上,自然会惹得他不痛快。
而李秋生呢,他早知晓这方子非原先那方子,只是借着这交方子一事,洗去自己的嫌疑。
他将方子交给孟泽了,已是谨慎之至,而验是孟泽验的,之后再察觉到不对,药方已在茶庄,孟泽只会怀疑那笃定的验方之人,很难怀疑到自己头上。
李秋生不由想起宁芙来,她心中大抵是胸有成竹,自己对婧成有情,而自己若是没有,大概认不出变化如此之大的婧成,只有时时放在心上,才能察觉到她那般多的细节。
退一万步而言,即便有那么一丝可能,自己不喜欢婧成,却偏偏认出了她,还怀疑宁芙给她的药方不简单,这方子,未必就能被查出不对劲。
且孟泽与宗肆,在李秋生看来,是一伙的,他抿心自问,如若不想救婧成,需要先替自己开脱,他是否会将药方交出来?
不会的,他会当做什么也未生,将这药方留在茶庄便是,自己初来乍到,怎会去得罪宣王府,便是有阴谋,为了避免自己卷进去,也会当做什么也不知道。
不深究药方,大抵能相安无事,几方相斗,也未必能查得这般细致,而一旦深究,自己有了宣王府把柄,那离死就不远了。
宁芙算准的,就是他如今在京中,不会冒险去惹事。
……
屈阳回到王府时,世子正与世子妃一块在荡秋千,世子妃坐着,世子则替她荡。
自屈阳跟了宗肆开始,也从未见过他这般有耐心的模样,便是凝姑娘小时候求他玩秋千,世子也难得理会。
屈阳暗道,也难怪凝姑娘在自己面前抱怨世子双标了,世子在世子妃面前,可不正是一副不值钱的样子……
前些时日,那些幕僚来书房,恰巧书房中还有世子妃留下的书,世子也是一本本记好她看到何处,亲自将书放好,从容道:“等我一盏茶的功夫,我将我夫人的书理好。”
幕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好道:“世子妃与世子真恩爱。”
宗肆似有些无奈,淡声道:“夫妻之间,便是得在这些小事上包容。”
屈阳当时想,这可并非是包容,这分明是甘之如饴。
“世子,世子妃,李大人离开茶庄后,就去了六皇子府。”屈阳上前道。
宁芙的心情,便放松了些,看向宗肆道:“李秋生对婧成有意。”他去了孟泽府上,心中是笃定这药方没问题,而为何会笃定,自然是明白了她的用意。
但凡李秋生不想插手婧成的事,就不会这般果断,而是会掂量掂量得不得罪得起宣王府。
宗肆道:“倒是未想到。”他有些好奇,孟渊若是知晓此事,会是何种心态。
几日后,茶庄的杳杳姑娘,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出现在了偏远的小巷之中,进了座破落的宅子,过了一炷香的功夫,又从那宅子中,走了出来。
身后有人跟着她,她也未察觉。
……
敬文帝与孟渊,一局棋落时,身边伺候的侍女,猫腰而来,附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
敬文帝抬头看了一眼孟渊。
“张珩之死,可有结果了?”身为父亲,身为帝王的那位,似是随口问了一句。
事到如今,自然并非毫无头绪。
不是孟泽所为,但要往孟泽身上推,也能有理有据,能做到毫无破绽。
但孟渊这几日,已猜出敬文帝的想法,他在试探自己,只要自己将张珩之死,有半点往孟泽身上推的嫌疑,那便是自己居心叵测。
他已在怀疑,自己对皇位,也有意思。
孟渊想起那日,敬文帝所言那句,“老三,你不要让朕失望。”
他所说的,是真相,也不只是真相,还有他孟渊,是否如表面那般老实,如若他野心勃勃,那便是让他失望了。
孟渊抚了抚手上的棋子,不太在意道:“儿臣觉得张珩之死,并非是六弟所为,也不想让六弟背这锅。”
即便眼下,敬文帝立储在即,孟渊急需抓住孟泽的错处,可也不得不放弃这次机会,谨慎为之,即便若是孟泽当了太子,自己再争那个位置,要难上数倍。
敬文帝却是一句话都未再多言,良久才道:“有人怀疑你,与胡人,也有些牵连。”
孟渊一顿,却是不顾那条伤腿,下跪道:“父皇若是怀疑我,不如杀了我。”
“我不怀疑你。”敬文帝将他搀扶起来,似乎是心疼道,“你既不图这皇位,如何会与胡人有牵连。”
这话分明是不信任自己,孟渊抿唇,蹙眉道:“父皇。”
“早日将张珩之事查清,给父皇,给你六弟一个交代,父皇年纪大了,耐心也不如从前多了。”敬文帝有些遗憾地道,“不要让父皇久等。”
张珩之死,孟渊只隐隐觉得受阻,似离那真相,只有一步之遥,却难以推进,自然是有人刻意为之。
他心中有数,敬文帝既怀疑自己,那么他手中,怕是有自己设计孟泽的证据。
如今如何让敬文帝手中的证据,与自己无关,是关键。
他如今只担心婧成的安危,敬文帝一旦怀疑他,势必会彻查他身边之人,他不担心被折了臂膀,却不能失去婧成。
孟渊垂下眼皮,眼底森冷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