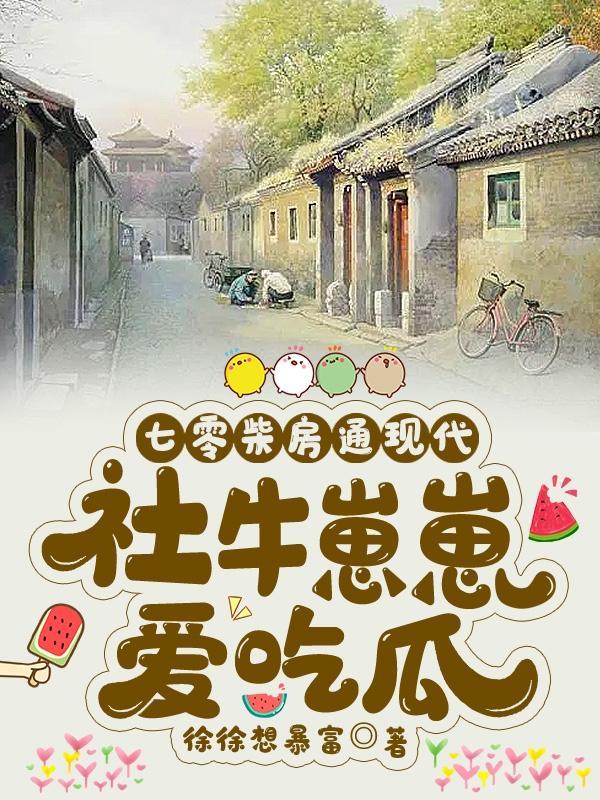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女尊:陨落后,他们求我别摆烂 > 第73章 我们这些棋子都懂规矩(第2页)
第73章 我们这些棋子都懂规矩(第2页)
木门重重关上,落锁的声音像锤子砸在安修鹤心上。
他僵在原地,看着自己身上那件石青色常服——料子还是上好的云锦,此刻却沾了泥污,袖口被磨破了边,露出里面白净的衬布。
这是他特意换上想求陛下怜惜的衣裳,如今却成了这破败地方的笑话。
他指尖颤抖着抚上自己的脸。
方才被拖拽时,额头磕在门楣上,此刻摸上去一片黏腻,他凑到漏进来的雪光里看,指腹竟沾了点血。
那是他最在意的脸。
是能让冷月翎偶尔失神的脸。
是他在后宫立足的根本。
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刮得他脸颊生疼,像无数根细针在扎。
他想起上元节的花灯,想起寒夜的汤药,想起自己簪着白玉簪站在宫道上时,宫人羡慕的眼神——那时他以为,凭着这张脸,总能在这后宫里挣得一席之地。
可现在,他连宁凡那个老男人都够不着了。
夜深时,寒气浸骨。
安修鹤蜷缩在柴草堆里,浑身冻得僵。
他下意识地拢了拢衣襟,却摸到袖口的破洞,指尖顺着破口探进去,触到自己光滑的皮肤——还好,脸没破,身子还在。
也许……也许陛下只是一时生气。
等她气消了,想起从前的情分,总会放他出去的。
他这样想着,竟迷迷糊糊睡着了。
梦里又是上元节的城楼,冷月翎穿着明黄斗篷,笑着把一盏兔子灯塞到他手里,说:“修鹤,这灯配你。”
此时,冷月翎正静静地站在他的床边,他的身体蜷缩成一团,眉头紧蹙,睡得并不安稳。
“风十,派人给安家传信。凌冬将至,极北地区必有一批穷苦百姓熬不过这个冬天,让安家去北方施粥放粮,花费的银钱从朕名下的商铺过。”
“接着,安排人为安家善行造势,命人在市井大肆传唱,朕要封赏安家。”
“是。”风十的声音从暗处传来,接着便是一阵窸窣声,她已经去着手安排了。
安修鹤醒来时,天刚蒙蒙亮。
嬷嬷的骂声已经在院外响起:“还不起?等着伺候的不成!”
安修鹤猛地坐起,柴草屑粘了满身,额角的伤口结了痂,又疼又痒。
他踉跄着起身,推开房门,看见院里堆着半人高的柴禾,还有两只空荡荡的水桶。
雪光落在他脸上,他下意识地抬手挡了挡——从前这个时辰,他该在镜前细细描眉,用上好的香膏护着皮肤。
可现在,他得去劈柴,去挑那结着薄冰的河水。
指尖触到冰冷的斧头时,安修鹤忽然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
他抡起斧头,重重劈在木头上。木屑飞溅起来,擦过他的脸颊,留下一道浅痕。
他没躲,只是咬着牙,一下又一下地劈下去,只是斧头落下的间隙,他总会不自觉地望向乾坤宫的方向。
那里,曾有他最渴望的恩宠。
而现在,只剩一道冰冷的、再也跨不过去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