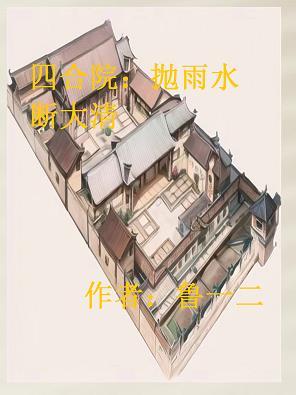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带着夫郎打天下 > 第3章(第3页)
第3章(第3页)
然而,景谡像是根本没听见他的声音,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座孤坟上。
“挖。”景谡的声音平静得令人胆寒,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给朕将他挖出来。”
侍卫们面面相觑,掘坟曝尸,这是何等骇人听闻、天理难容之事!但天子之令,无人敢违抗。
“陛下!”大内侍劝阻,“左都尉已入土为安,逝者已逝,此举惊扰恐……恐有不祥!陛下三思啊!”
景谡终于垂眸瞥了他一眼,他淡淡地吐出两个字:“拖开。”
立刻有侍卫上前,将大内侍拖拽到一旁。
侍卫们并没有带锄头和铲子,于是只能用剑柄或是徒手挖坟,泥土砂砾被不断翻开。
景谡就站在坑边,一动不动地看着,眼底的赤红越明显。
忽而,一侍卫手中的剑砸到了一处硬块,那是终于裸露出来的骸骨。
段令闻下葬,甚至没有入棺,只用一张草席裹尸入土。随着时间的流逝,草席已经腐朽风化,那森白的骸骨就这么突然暴露了出来。
侍卫们不敢再贸然挖掘,有人将剑放下,正欲动手拨开泥土砂砾。
“退下。”景谡冷冷道。
侍卫们闻言,立即躬身退至一旁,不敢再多看一眼那暴露出的白骨,更不敢揣测圣意。
景谡一步步走下土坑,他半跪在地,伸手拨开覆盖在尸骨上的泥土。
趾骨、臂骨,肋骨,脊柱……头颅。
景谡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那肩胛骨上的伤痕,那是几年前,宛城一战,段令闻以身为他挡了一箭,这道伤痕深入骨髓,触目惊心。
这……就是段令闻的尸骨。
一年时光,血肉尽消,曾经温软的身躯只剩下一具森白的骸骨,安静地躺在那里。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凝固,所有喧嚣、嘶吼、哭泣都骤然远去。
景谡脸上的疯狂和焦躁退去,只剩下一种近乎茫然的空白。他怔怔地看着那具骸骨,然后,他极其缓慢地、颤抖地伸出手,轻轻地、轻轻地触碰上那颅骨的额际。
一滴滚烫的泪水毫无预兆地从景谡赤红的眼眶中砸落,正好落在那森白的头颅上,洇开一小片湿痕,随即迅被晨风吹得冰凉。
巨大的悲恸,将他整个人彻底淹没。
此刻,这方小小的土坑里,仿佛只剩下他和那段沉寂了多年的过往。
九砾山上,晨风吹过,卷起沙砾,一片死寂。
大内侍跪在地上,颤巍巍上前来,劝道:“陛下,请令左都尉入土为安吧……”
良久,景谡终于开口,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带着一种扭曲的怪异,“这里孤寂,朕……要带他回家。”
段令闻的家在吴县段家村,大内侍是知道的。而且,当时段令闻饮鸩自尽时,他的遗书上也希望落叶归根。
如今一年过去,陛下终于答应。
于是,大内侍的心稍稍放松了些,他连忙道:“奴才这就去准备迁葬一事。”
景谡充耳不闻,他脱下自己的外袍,竟像是怕惊扰了谁一般,极其轻柔地将那具骸骨仔细包裹起来。
而后,将其抱起。
段令闻已经没有家了,而自己就是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