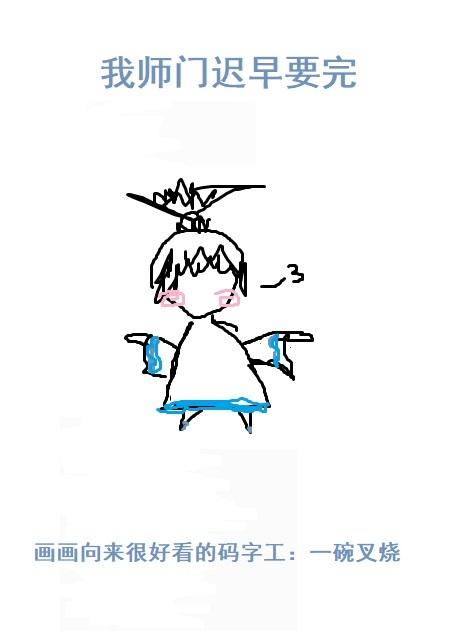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九州民间志 > 第71章 冥婚轿(第1页)
第71章 冥婚轿(第1页)
开春的雨总黏黏糊糊的,把平江府外的陈家村泡得潮。阿景蹲在自家作坊的门槛上,手里攥着块刚刨好的楠木片,木头上的纹路被雨气浸得亮,像极了他阿爷生前留下的那把旧梳子。作坊里飘着淡淡的松烟味,是师傅老周头在熬漆——朱红的漆,熬的时候要加桐油,还要搅上整整一个时辰,不然刷在木头上会裂。
“阿景!把那堆樟木方子挪到檐下,别让雨泡坏了!”老周头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带着点咳嗽,烟袋锅子在门槛上磕了磕,火星子落在湿泥里,“滋”地一声就灭了。
阿景应了声,起身搬木头。樟木沉,他才十七,胳膊上的腱子肉还没长实,搬得慢了些,老周头就拄着拐杖走出来,看他的眼神像看块没雕好的料子:“慢些没事,仔细别砸了脚。咱们做轿子的,手上得有准头,脚下也得稳,不然做出来的轿子,抬着人走不稳当。”
阿景点点头,把最后一块樟木挪好。这作坊是老周头传下来的,打从阿景爹娘走得早,他就跟着老周头学做轿子,一晃五年了。陈家村附近的人娶媳妇,多半来这儿订轿子——红漆的轿身,雕着缠枝莲,轿顶安着锡做的宝顶,四角挂着铜铃,抬起来“叮铃叮铃”响,喜庆得很。可阿景从没做过另一种轿子——老周头偶尔提过一嘴,说以前做过“冥轿”,是给故去的人办婚事用的,也就是人常说的“冥婚”。
“那冥轿,跟活人用的轿子不一样吗?”阿景以前问过一次,老周头当时正抽着烟,半天没说话,最后只说了句“差不多,又差得远”,就没再往下讲。
这天的雨下到傍晚才停,天边染着层淡淡的橘色,阿景正收拾工具,就听见巷口传来脚步声,还带着点细碎的啜泣。抬头一看,是村西头的阿桃,穿着件洗得白的青布襦裙,手里攥着块蓝布帕子,眼睛肿得像核桃。
“阿景哥,周师傅在吗?”阿桃的声音带着颤,说话时还吸了吸鼻子,帕子捏得更紧了。
老周头从里屋走出来,看见阿桃,眉头皱了皱:“是阿桃啊,有事?”
阿桃咬了咬嘴唇,像是鼓足了勇气,才开口:“周师傅,我……我想请您做顶轿子。”
老周头“哦”了声,伸手摸了摸烟袋:“是你要嫁人了?日子定了?”
阿桃的脸一下子白了,眼泪“啪嗒”就掉在地上,砸在湿泥里,晕开一小圈印子:“不是我……是我哥。我哥他……他去年冬天没的,我爹娘想给他办场冥婚,找个‘媳妇’,好让他在底下不孤单。”
这话一出,作坊里一下子静了,只有檐角的水珠还在往下滴,“嘀嗒,嘀嗒”,像敲在人心上。阿景站在旁边,手里的刨子差点掉在地上——他知道阿桃的哥,叫阿松,比他大两岁,以前常一起在河边摸鱼,去年冬天去山里砍柴,遇上大雪,滑下山崖没了,才二十岁。
老周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开口:“冥婚轿,我有好些年没做了。你爹娘……想好了?”
“想好了,”阿桃的声音更颤了,“找的是邻村李家的姑娘,去年夏天没的,也是年纪轻轻。李家同意了,说下个月初六是良辰吉日,想让我们……让我们把轿子做好。”
老周头叹了口气,转身往作坊里走:“进来吧,说说要求。阿景,你也过来听着,搭把手。”
阿景跟着进去,作坊里的樟木味和漆味混在一起,闻着有点闷。老周头坐在靠窗的矮凳上,让阿桃坐下,又给她倒了杯热水:“冥婚轿,看着跟活人用的喜轿像,但讲究不一样。先说木料,不能用松木,松木易裂,不‘稳’;得用楠木或者樟木,楠木防潮,樟木避虫,底下的人用着‘安心’。”
阿桃点点头,把杯子握在手里,像是能从里面汲取点暖意:“都听师傅的,您说用什么就用什么,钱我们家会凑齐的。”
“钱的事不急,”老周头摆摆手,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泛黄的纸,展开来,是张轿子的图样,上面画着顶四方轿,轿身雕着花纹,只是花纹比活人用的简单些,“你看,这轿身要朱红漆,跟活人婚礼的喜轿一个色,图个‘喜庆’,也让底下的人觉得跟真的一样。但轿帘不能用红绸,得用青布,青布压惊,免得‘惊’着新娘子。”
阿景凑过去看,图样上的轿门旁边,还画着两个小小的纸人,一个男一个女,穿着宋朝的衣冠,男的戴幞头,女的梳高髻。老周头指着纸人说:“轿子里得放一对纸人,替你哥和李家姑娘坐着。纸人要找纸扎匠做,得跟真人差不多高,衣服要绣花纹,男的绣兰草,女的绣海棠,都是宋朝民间喜欢的纹样,吉利。”
阿桃一边听,一边用帕子擦眼泪,擦得眼睛更红了:“我哥生前最喜欢兰草,去年春天还在院子里种了几棵,说等开花了给我看……”话说到这儿,又哽咽了,说不下去。
老周头没说话,只是把烟袋拿出来,又没点,就那么捏在手里。阿景看着阿桃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阿松哥以前总帮他修渔网,还教他爬树掏鸟蛋,那么好的人,怎么就没了呢?他想起去年冬天,阿松没了的那天,村里的人都去帮忙找,最后在山崖底下找到的时候,人都冻僵了,阿桃哭得晕过去好几次。
“师傅,”阿景忍不住开口,“这冥婚轿,做起来跟平常的轿子里,步骤一样吗?”
“差不多,但有几处要特别注意,”老周头终于点了烟袋,吸了一口,烟雾从他嘴角冒出来,模糊了他的皱纹,“第一,轿底要钉七根桃木钉,桃木能辟邪,免得有不干净的东西跟着。第二,轿子里要放一小袋米,米是粮食,象征着‘有吃有穿’,底下的人也得过日子。第三,轿顶的宝顶不能用锡的,要用纸糊的,外面刷层金粉,锡是金属,太沉,‘带’不走。”
阿景把这些都记在心里,拿出个小本子,用炭笔写下来——他识字不多,是老周头教的,平时做活记尺寸、记步骤,都靠这个小本子。老周头看他写得认真,点了点头:“明天你去后山的林子里,挑一根楠木,要直的,没有结子的,回来咱们先开料。记住,挑的时候要对着太阳看,木头上的纹路要顺,顺纹的木料结实,做出来的轿子不容易坏。”
“哎,知道了师傅。”阿景点点头。
阿桃又坐了一会儿,跟老周头敲定了轿子的尺寸,说过两天让她爹来送定金,然后就起身告辞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看作坊里的木料,又看了看阿景,轻声说:“阿景哥,麻烦你了。”
阿景摇摇头:“不麻烦,阿桃姐,你别太难过了,阿松哥知道你们这么为他着想,肯定会高兴的。”
阿桃没说话,只是笑了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然后就转身走进了暮色里。巷子里的灯笼已经点上了,昏黄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走一步,影子就晃一下,像个没根的草。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阿景就背着斧头和锯子,去后山挑楠木。后山的林子很密,早上的雾还没散,空气里满是树叶和泥土的味道。阿景沿着小路走,眼睛盯着路边的楠木,一根根看过去——有的太细,有的有结子,有的纹路不顺,都不符合老周头的要求。
走了快一个时辰,才在林子深处找到一根楠木,有碗口那么粗,直溜溜的,没有一个结子,对着晨光看,木头上的纹路像流水一样顺。阿景高兴坏了,放下工具,先绕着楠木走了一圈,用手摸了摸树皮,糙糙的,带着点湿意。
“就你了,”阿景对着楠木说,“你可得好好的,做成轿子,送阿松哥一程。”
说完,他拿起斧头,开始砍树。斧头下去,“咚”的一声,震得他手有点麻,楠木太硬了,得一点一点来。砍了一会儿,他额头上就出汗了,脱了外面的短打,只穿件单衣,继续砍。阳光慢慢升起来,雾散了,林子里的鸟开始叫,叽叽喳喳的,倒是不显得孤单。
砍到中午,楠木终于倒了,“轰隆”一声,压断了底下的几棵小树。阿景坐在地上,歇了会儿,吃了点带来的干粮——是阿桃昨天送来的麦饼,还热乎着。他咬了口麦饼,想着阿桃的样子,又想起阿松哥,心里酸酸的。
下午,他用锯子把楠木锯成几段,又用绳子捆好,扛在肩上往回走。楠木很重,压得他肩膀生疼,走几步就得歇一下。走到半山腰的时候,遇见了村里的王大爷,王大爷背着一捆柴,看见他扛着楠木,就问:“阿景,你扛这么粗的楠木,是要做什么?”
“王大爷,是给阿桃姐家做冥婚轿用的,”阿景说,“阿松哥要办冥婚,师傅让我挑根好楠木。”
王大爷叹了口气:“阿松这孩子,命苦啊。办冥婚也好,免得他在底下孤零零的。不过话说回来,这冥婚轿可有讲究,我年轻的时候,见过一次冥婚轿抬上山,那轿子里还放着新娘子的衣冠,抬轿的人都说,走的时候觉得轿子特别沉,像是里面真有人坐着似的。”
阿景愣了愣:“真的吗?”
“都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谁知道是真是假,”王大爷笑了笑,“不过你做的时候可得仔细点,别出什么差错,对底下的人不敬。”
阿景点点头,谢了王大爷,继续扛着楠木往回走。回到作坊的时候,老周头已经在等着了,看见楠木,满意地点点头:“不错,这根木好,没选错。”
接下来的几天,阿景就跟着老周头一起做轿子。先是开料,把楠木刨平,做成轿身的框架,老周头教他怎么用刨子,力道要均匀,不然刨出来的木头不平整。阿景学得很认真,手上磨起了水泡,他也不吭声,只是晚上用热水泡一下,第二天继续做。
做框架的时候,老周头给阿景讲了宋朝冥婚的规矩,都是他从师傅那里听来的,还有些是从《东京梦华录》里看来的——老周头识些字,家里有本旧的《东京梦华录》,是他爹传下来的。
“你知道吗?宋朝民间办冥婚,跟活人婚礼差不多,也得有媒人,叫‘冥媒’,”老周头一边刨木头,一边说,“还得交换庚帖,不过是纸做的,上面写着故去人的生辰八字,得请先生算过,合得来才能办。还有聘礼,也是纸做的,比如纸房子、纸车马、纸家具,都是按活人用的样子做的,烧给底下的人用。”
阿景一边听,一边点头,手里的活也没停:“那抬冥婚轿的时候,也得有吹鼓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