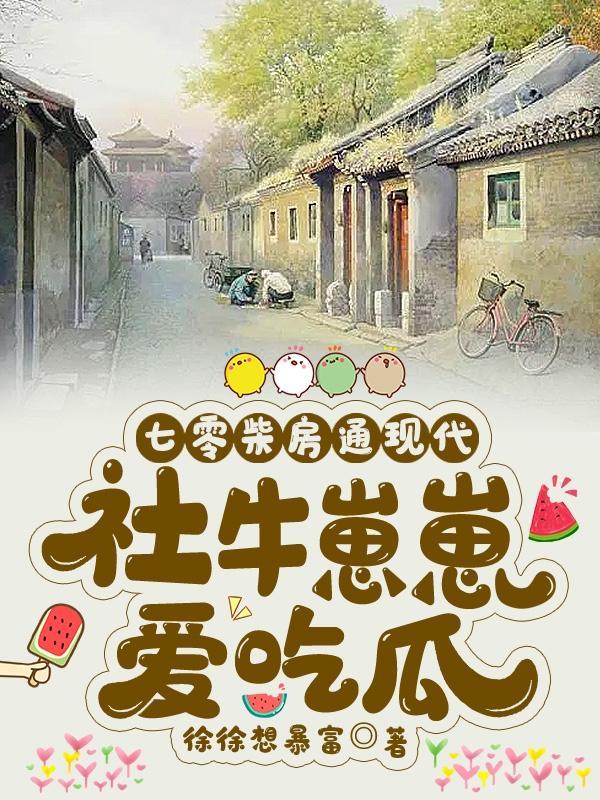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捕刀人 > 第477章 雪地血战(第1页)
第477章 雪地血战(第1页)
寒雪裹着碎冰碴子打在脸上,壮汉粗糙的手掌像铁钳似的扣住刘柯脚踝,冻得僵的嘴角咧开一道狞笑:“小子,在这雪地里跟咱们玩花样,还是太大意了。”
话音未落,他猛地从半人深的积雪里蹿出,胳膊上虬结的肌肉贲张,像拎小鸡似的将刘柯倒提起来。
雪沫子顺着刘柯的梢往下掉,他却没半分慌乱,只垂着眼看柴朔朝不远处的雪地喊:“公主,这小子看着花哨,实则……”
“柴朔,小心!”
另一个壮汉的嘶吼像炸雷般劈来,柴朔后颈的汗毛瞬间竖了起来。
他低头一看,掌心里哪还有什么活人?只有一枚巴掌大的红色印记,像烧红的烙铁似的烫得他掌心麻。
“再见。”
清淡的笑声从身后飘来,柴朔刚要转头,就见刘柯站在三丈外的雪坡上,指尖轻轻一握。
那枚红印瞬间炸开,赤红色的气浪裹着碎雪翻涌,柴朔瞳孔骤缩,猛地将体内暗劲全聚在胸前——他常年在关外厮杀,练过一门“铁石身”的硬功,此刻竟也被气浪掀得连连后退,左臂传来一阵钻心的剧痛。
低头时,他才看见自己的左臂齐肩而断,断口处的血瞬间被寒气冻成了暗红的冰碴,“嗬……”他闷哼一声,咬着牙用右掌按住伤口,眼底满是惊怒。
就在这时,一道低沉的念咒声在雪地里响起,像是从远古传来的钟鸣。
“近及远,远及近,心烛渊,法无道,钟天临,辰晚云,破天工,一气尽,万道音!”
是老四沈烈!刘柯刚稳住身形,就见那个一直站在最后、脸上有道刀疤的壮汉抬了抬手。
他的衣袖不知何时被气劲震碎,两条手臂上竟密密麻麻布满了铜钱大小的孔洞,像是被百箭穿射过的筛子。
沈烈双手在胸前一碰,那些孔洞里突然溢出淡金色的光,下一秒,刺耳的音波如同实质的利刃,从他掌心炸开!
刘柯只觉得耳膜像被重锤砸中,脑子里“嗡”的一声,整个人像断线的风筝似的往后飞出去,后背重重撞在一棵老松树上。
松枝上的积雪“哗啦”一声砸了他满头满脸,喉间一阵腥甜,他猛地咳出一口血,血滴落在雪地上,瞬间凝成了小红珠。
还没等他撑着树干站起来,一阵狂风突然从斜刺里卷来。
是先前夺了他刀的老三周虎!只见周虎深吸一口气,胸膛鼓得像个皮囊,接着猛地一拍自己的小腹,“哈”的一声暴喝,一股肉眼可见的白色气浪从他口中喷出,像奔腾的野马般撞向刘柯。
刚站稳的刘柯再次被狂风掀翻,踉跄着退了十几步才勉强撑住膝盖。
雪地里留下两道深深的足印,他低头看了眼自己被气劲震裂的衣襟,肩头的伤口正汩汩往外冒血。
“玩够了?”
刘柯轻笑一声,抬手在肩头伤口处一扯。
众人只觉眼前红光一闪,他竟从血肉里硬生生拽出一杆三尺长的红色长枪——枪身像用凝固的血铸造成的,枪尖泛着冷冽的光,枪尾还挂着几缕没扯断的血丝。
不等众人反应,刘柯脚下一点,身形如箭般朝沈烈刺去。
沈烈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双臂再次往胸前一撞,比刚才更刺耳的音波炸开,空气中仿佛都泛起了涟漪。
“铛”的一声脆响,刘柯的血枪竟被音波震得寸寸碎裂,化作漫天细密的血滴,悬在半空中,像无数根锋利的血钉子。
“有点意思。”
刘柯挑眉,指尖轻轻一动。那些血滴瞬间调转方向,带着破空声朝沈烈、周虎几人射去。
“不好!”